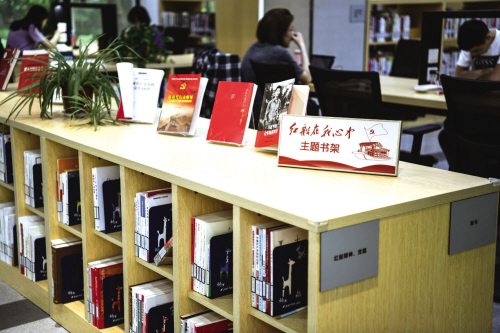新塍镇郭厅弄的老屋里,一扇绿色木窗上挂着一溜彩色鹅蛋,阳光透过窗棂,在光洁的蛋壳上投下斑驳光影——孩童憨态可掬,山水层叠有致,花鸟振翅欲飞,这些毫厘之间的微观世界,全出自83岁非遗传承人许欢欢的一双巧手。
“小时候家里翻到一对彩绘鹅蛋,上面画着玩耍的孩童,颜色虽淡了,可那股子灵动劲儿,我记了一辈子。”许欢欢坐在桌前,眉眼带着笑意,狼毫笔蘸着颜料,正为一只鹅蛋勾勒孩童的发梢。她身后的展示架上,上百枚彩蛋层层叠叠,像一串凝固的时光,串起她与非遗的半世纪情缘。
与画结缘:书香门第里的“童年启蒙课”
许欢欢的非遗基因,藏在“书香门第”的底色里。她的爷爷是嘉兴秀才,父亲是当地医生,家中虽无专门的画室,却总飘着墨香。“有几位书画家常来家里串门,我蹲在边上看他们挥毫,小手指在地上画,慢慢就入了迷。”

真正与彩蛋画结缘,是一次偶然的发现。“小时候翻旧物,找到一对彩绘鹅蛋,上面的孩童活灵活现。”她回忆,“那时候物资匮乏,长辈们有喜事就画彩蛋当礼物,画个花鸟、孩童,既喜庆又有文人趣味。”这份童年的惊艳,成了她后来重拾彩蛋画的“初心”——退休后,她加入嘉兴市鸳鸯湖诗画社,在老年大学系统学画,终于圆了“把彩蛋画传承下去”的梦。
匠心独运:蛋壳上的“微观世界”

彩蛋画,是“小”与“精”的艺术。鹅蛋直径仅六七厘米,表面弧度凹凸,要在上面画山水、人物、花鸟,比纸上作画难十倍。“得先勾草图,算好布局,否则一笔错,整颗蛋就废了。”许欢欢说。

她的彩蛋有个鲜明特点——90%都是孩童主题。“小孩最有灵气,眼睛里有光,画他们最能传递希望。”展示架上,一枚鹅蛋上的孩童正踮脚捉蛐蛐,发辫翘起,衣袂翻飞;另一枚上,两个孩童抱着鲜果嬉闹,项圈上的“长命百岁”字样清晰可见。“这些都是我观察生活画的,有的像邻居家的娃,有的像自己孙辈,越画越有温度。”

每枚彩蛋的诞生,都藏着老两口的默契。老伴黄观生负责“后勤”:挑蛋(选圆润的鲜鹅蛋)、掏蛋液(用细针在蛋壳两端钻孔,吹出蛋液)、打磨(用砂纸将蛋壳磨得光滑)。“他总说‘你负责画,我负责让蛋听话’。”许欢欢笑着指了指老伴——此刻,老人正坐在藤椅上,握着砂皮纸轻磨一枚新蛋,阳光洒在两人斑白的发间,像一幅岁月静好的画。
非遗传承:课堂里的“文化接力”

“非遗不能‘锁在柜子里’,得让年轻人摸得着、画得乐。”这是许欢欢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每周五下午,新塍镇的杭州师范大学附属磻溪小学里,都能见到许欢欢的身影。“我给孩子们带了‘特殊作业’——在蛋壳上画自己喜欢的东西!”课堂上,她先示范勾线、上色,再让孩子们自由发挥:有的画奥特曼,有的画小花猫,有的画“全家福”……“一开始担心他们觉得‘老土’,结果孩子们说‘在蛋壳上画画像变魔术,很有趣!”


教学近十年,她摸索出一套“渐进法”:第一学期打基础,让孩子自由创作;第二学期定主题,比如“24节气”“传统节日”,“既保留兴趣,又植入文化”。去年,她带的小学生用彩蛋画“24节气”,春分画燕子衔泥,冬至画围炉煮茶,作品在学校展出时,家长们感慨:“原来老祖宗的节气,能这么可爱!”

“有人怕‘传出去就没价值了’,我偏要‘掏心掏肺’教。”许欢欢说,“我岁数大了,希望孩子们早点接棒。”
家传温度:纸伞灯彩里的“喜悦与坚守”

除了传承彩蛋画,许欢欢还是省级非遗项目纸凉伞灯彩的传承人。
纸凉伞彩灯不是普通用来遮阳避雨的伞,而是清朝以来流传的一种独特的民间灯彩,珍贵之处在于它精细的制作工艺。

今年,许欢欢和老伴为孙子婚礼特制了纸凉伞灯彩,这盏高2.1米的纸伞,骨架由老伴手工扎制,伞面的古代侍女图全由许欢欢绘制。“原本想画《红楼梦》《西厢记》,但时间紧,就挑了最擅长的侍女主题。”她指着伞面,“你看这衣纹的线条,得一笔笔勾,不能断;颜色要淡,透光才好看。”
制作周期整整半年。八旬老两口每天要花上好几个小时的时间,“眼睛花了就休息一下,手酸了就揉一揉。”但他们说“值”:“这把纸凉伞灯彩不仅是给孙子的新婚礼物,更是把非遗的‘喜’传给更多人。”

暮色漫进老屋,许欢欢放下画笔,轻轻擦拭刚完工的彩蛋。窗外,老伴正把新打磨好的鹅蛋收进竹篮。“只要画得动,我就一直画;只要孩子们愿学,我就一直教。”她望着满架彩蛋,目光温柔,“非遗不是老物件,是活的——你看,这蛋壳上的孩童在笑,纸凉伞灯彩上的侍女在盼,他们都在说:‘我们看到了非遗的未来,还在传承。’”


这,或许就是非遗最动人的模样:有人守着,有人爱着,有人传承着。